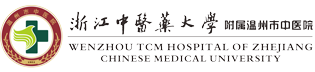春来荠菜香
春天,如果你没能吃上至少一次荠菜,那实在是遗憾呢。
在北方,农历的二三月,是野生荠菜生长旺季,尤其清明前后,田野、路边、山脚,随处可见。它不择土壤,其貌不扬,羽毛状的叶片匍匐于地,灰头土脸的,和钻出地皮的野蒿、蒲公英混在一起,让不识者难以分辨。早春,常有人提着大大的袋子到田野里挖荠菜,土质松软的树下,或是还未翻耕的农田,是荠菜最喜之地,这样地界长出的荠菜细嫩,很有菜的模样。
但荠菜的喜人不在这里,而是它见水后的样子。采来的荠菜择洗完毕,不似苦荬菜那样可以直接入口,而是需用开水焯一下,捞出,放清水里冷却后才能食用。看吧,经过热水翻滚了的荠菜,转眼嫫母变西施,成了出水芙蓉,碧绿碧绿的,似翠,如玉,那绿纯粹、干净、清透、诱人。这时的荠菜怎么吃怎么好,凉拌、做汤、做馅,都是少有的美味。尤其做馅,那香清清的,淡淡的,有田野自然之清气回旋齿间,说不清,道不明,没有任何一种菜堪比。
荠菜富含多种有益成分,不仅老百姓喜欢,历代王公贵族们也争相品尝,更有苏轼“天然之珍,虽小甘于五味,而有味外之美”的赞誉,其特殊的芳香深得苏子之心。
每年春天,二姐都要拉着我走向田野,挖荠菜于她是雷打不动的仪式。春起的荠菜最为鲜嫩,待荠菜开出米粒似的小白花后就老了,一般就没人再去采食了。但二姐依然去采,鲜嫩的,二姐焯水,攥团,放冰箱里冷冻着,从春吃到冬。开了花的,二姐择净晒干装枕头,祛火安眠。荠菜早被李时珍记入《本草纲目》,民间也多有偏方。想来二姐是深谙荠菜功效的吧。多年前,二姐夫中风留下后遗症,几次都是二姐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。二人年轻时感情并不好,经历岁月风霜后,竟懂得了相惜相携。二姐每天为二姐夫按摩,自创的一套手法连按摩师傅都感佩。枕着二姐年年更换的荠菜花芯枕头,二姐夫望向二姐的目光温柔又踏实。
也许,世事就是这样,最可贵的也最日常,就像荠菜,沉寂了一冬,把最醇美的芳华奉献大地时也是不声不响、毫不起眼的。识得的,自然懂;漠视的,便也错失了一种美好。
曾看到过著名作家王祥夫的一篇文字,说的是他吃荠菜包子,大呼其美味,但他没见过真正的荠菜长什么样,便四处问询。我在心里真是替他、也替荠菜,感到遗憾。王祥夫是作家,也是画家,如果他见了荠菜的平凡样貌,是否会为这人间珍馐而一付丹青,也说不定呢。
想起去年夏天,和朋友去密云古北水镇游玩,中午去一农家院吃饭时,竟碰到了儿时的玩伴聋丫。相隔三十几年,我和聋丫几乎喜极而泣了。聋丫因幼时生病高烧,致使耳朵半聋,没能上学。有年春天,我俩一起去河边挖野菜,因为一棵荠菜到底是谁先发现的,而打了起来。饥馑的年月里,我们因一株弱小的荠菜而大打出手。最后,荠菜被撕扯粉碎而随流水漂走,我和聋丫也好长时间互不理睬。后来,我上了大学,二十岁不到的聋丫被父母嫁进了长城脚下的山里。丈夫是健全的,只因家穷才娶了聋丫。没想到,数十年后,天翻地覆,这里整体搬迁,昔日穷山沟,一下子变身为享誉京畿的古北水镇。聋丫家享受到了优惠政策,开起了农家院。如今的聋丫二层小楼住着,儿女双全,孙子都会地上跑了。说起儿时趣事,聋丫也笑得开心。大声说笑间,她让服务员上了一份凉拌荠菜,又亲自下厨做了一份纯正的荠菜馅包子,直吃得我眼睛湿润。
聋丫懂得荠菜品性,她说凉拌和做馅最能吃出荠菜原味,许多人做馅喜欢放肉,其实不对,荠菜最好全素,佐料也只姜蒜就够了,如果非要放肉,也是猪肉,只一点点,千万不要多,提味足矣。
荠菜春天生长,夏季还能吃到,难得。不是贵客,聋丫断不会割爱。看着聋丫,想起小时候用来果腹的荠菜被她吃出了如此门道,不禁感慨。日子闲适富足了,才会有更加细腻的心思吧。把荠菜还原成荠菜原本的味道,不偏不倚,不浓不淡,是至味,也是对荠菜的一种体恤。
时至今日,那荠菜的清香还在舌尖、心底婉转回旋,一直未曾淡去。
(来源:北京日报 王也丹)
妙味的宣纸
很难想象,从未接触过的宣纸,竟能如此牵动我的情思。
皖南山水间,秋色迷离中,在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那泓水边,我结识了宣纸。于是,我进入她的世界,她融汇于我的梦中。
一袭蓝底白花,两袖乌溪清芬。披着江南的和风,甩着楚女的纤手,斜挂吴越印记的斗篷,她从盛唐的皖山徽水、丹霞薄暮中款款走来,如自身般轻盈飘逸……不是我非要把她想象成什么,而是想起宣纸,脑际就闪现这个画面。
在青弋江畔、乌溪水边,小岭檀林、沙土稻田,我试图捕捉她的身影,寻觅她的踪迹,素描她的容颜,理清“她和他”的关系,把故事还原到那过往的历史时空。
其实,我所追寻的答案已经明了。她的出现,何以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书画承载起独一无二的齐天书案,为中国绝无仅有的狂草书法、泼墨山水铺排开绝无仅有的无际画廊,那已经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,宣纸原本就是为中国书画而生。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汪洋恣肆,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的独步辉煌。这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把她们双双列入、一体对待就看得出来。
这样的绝配天下无双,如此的设计唯有天成!
宣纸因其“质地绵韧、光而不滑、洁白稠密、纹理纯净、搓折无损、不蛀不腐、润墨性强、韵感万变”的独特禀赋,成为古往今来中国书画家们的最爱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你看,铺开宣纸,勾勒、上墨、补笔;点色、墨破色或者色破墨、泼墨;焦墨宿墨理层次,铺水亮墨提精神……不大功夫,一幅典型的山水画便在国画大师的案头山隐水动,云行鸟藏。其中的墨分五色,洇随意至,虚实浓淡,氤氲自生,实在妙不可言。
这就是宣纸国画,也只能是宣纸国画!当然,行书狂草、古隶大篆之于宣纸更是生死绝配,命运搭档,不可能由其它什么纸张替代。
再打量宣纸本身,从她出生、成长、成名、走红,每一个节点都显现浓淡相宜的典雅,每一个转身都迸发无色无艳的华丽,掩饰不住一种质朴的美,绵柔的韧,清越的秀,成熟的韵,内敛的慧,持守的醇!
难怪郭沫若对她不吝褒词:“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作,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他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。”国画大师刘海粟更是赞誉有加:“纸寿千年,墨韵万变。”
艺术的妙味,妙味的艺术。千年纸寿,万变墨韵。能入泰斗大师的法眼,能启风流文豪的金口,宣纸的奇妙可见一斑。要说宣纸的妙味,首先在破蛹成蝶的过程。
显然是沾了黄山、九华山的秀气,得了巢湖、太平湖的灵气,泾县宣纸一出生就美妙可人,不同凡响。虽然诞生在遥远唐代,成长于偏僻泾县,经历了上千年岁月,但对于独占天时地利、绝活秘笈的宣纸来说,依然花信尚存,青春不衰。
地理地质、纬度湿度的恰到好处,使泾县乌溪当地的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,纤维柔韧绵密,质地纯正,远远优于他地。这恰恰是宣纸必需的、独特的制浆材料。而当地的两股山泉——一股偏碱、一股偏酸,为宣纸制浆时需要偏碱、捞纸时依赖弱酸的用水要求提供了恰到好处的保障。移作他地,无此水源,换在他乡,无此便当。事情就这么奇妙!
那天,在乌溪秋染多彩的山中,几座白雪皑皑的山岭突然撞入眼帘,犹如钻石镶嵌于翡翠斑斓之中,异常亮丽,格外醒目。行至近前才弄明白,这是宣纸的燎皮、燎草摊晒基地之一。
从原料开始,选、捡、蒸、煮、沤、浸、扯、晒,清除青檀树皮、沙田稻草的无用杂质,存留纤维精华,在这样的摊晒基地至少一年的不停翻覆,风吹日晒,雨淋雪冻,自然漂白,再经过蒸煮、碓捣、切碎、踩洗、过滤、打浆,然后再经搅拌、加药的调浆,经过工人用帘床、纸帘节奏适度的捞滤,悉心呵护的烤晒,剪裁果决的修边,缜密细致的封包,便成了成品宣纸。
成品宣纸看似单调,其实精彩纷呈。按加工方法分为原纸和加工纸;按纸张洇墨程度分为生宣、半熟宣和熟宣;按原料配比分为棉料、净皮、特种净皮;规格按大小有四尺、五尺、六尺、尺八屏、七尺金榜、八尺匹、丈二、丈六、二丈、三丈三;按丝路有单丝路、双丝路、罗纹、龟纹等。对生宣进行特种技术再加工,便成了蜡宣、矾宣、色宣、色矾宣等多样熟宣。若书法、写意宜用生宣,工笔作画宜用熟宣……
破蛹成蝶的整个工艺非常耐读耐看,妙趣横生。全程古法,不事添加;完全手工,不借机械。尽显一种古朴劳作,原始生产的画面感,漫溢一种不同工具声部搭配、节奏有板有眼的音乐感,一种亲手制作稀世珍品、共同打造传统经典的成就感,沁润一种相互独立又分工合作、上下搭配又自然流畅的程序美,一种肢体动作有张有弛、协调舒展的优雅美,一种当下难得一见的悠闲从容、步调不紧不慢的散淡美。
这情景很可能就开始于那久远的过去。那时坊东置坊,供奉蔡伦;开坑立槽,祭祀孔丹。匠人制纸,宛若祭拜神明,诚惶诚恐;犹如敬立图腾,饱含虔诚。每一工序都认真执着,尽心竭力。
这应该就是宣纸工人工匠精神的传承、宣纸业者百年老店的传统延续吧。在宣纸工坊,我看到,师傅们捞纸的步幅,抬腿投足,进退有据,难少半跬;晒纸的姿势,舒展洒脱,错落有致,不多一刷。匠人之于宣纸,犹如德人制车、瑞人造表、仁怀酿酒、宜兴烧陶,循规蹈矩,精益求精,不敢有丝毫懈怠,半点偷工。于是有了宣纸传至当今,一直不改质朴的脾性,稳固的品质。
在晒纸车间,我对一位光着脊梁、穿着裤衩儿的刷纸工人说:“小伙子,你知道吗?你是在用你这把刷子打磨人类的瑰宝,在用你的劳动创造绘画的艺术,用你的汗水书写文化的历史。”
他用臂腕杠了杠额头的汗珠,笑了笑:“哪有那么高的境界!我只知道咱得造好每一张宣纸,不能让传统手艺丢了,要对得起那些写字儿画画儿的。”
也许,这位身材瘦朗、技术娴熟的刷纸师傅,无意间道出了宣纸别样的妙味:人与纸、纸与史之间的微妙关系,精彩互动。
(来源:人民日报 戴鹏)